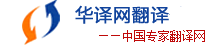|
 |
 |
《雷峰塔》和《易经》:
失败敲门砖
用英文创作的《雷峰塔》和《易经》部分重写了《小团圆》里面的故事,《雷峰塔》是张爱玲以自己四岁到十八岁的成长经历为主轴,糅合其独特的语言美学所创作的自传体小说。情节在真实与虚构间交织,将清末的社会氛围、人性的深沉阴暗浓缩在这个大家族里。《易经》接续《雷峰塔》的故事,描写女主角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的遭遇,同样是以张爱玲自身的成长经历为背景。张爱玲曾在写给好友宋淇的信中提及:“《雷峰塔》因为是原书的前半部,里面的母亲和姑母是儿童的观点看来,太理想化,欠真实。”相形之下,《易经》全以成人的角度来观察体会,也因此能将浩大的场面、繁杂的人物以及幽微的情绪,描写得更加挥洒自如,句句对白优雅中带着狠辣,把一个少女的沧桑与青春的生命力刻画得余韵无穷!
事实上,《雷峰塔》和《易经》是张爱玲在1960年代转向英美文坛创作的失败敲门砖,最初共800多页,30多万字,因篇幅太长而一拆为二。“《雷峰塔》、《易经》,下接《小团圆》,按理可称为张爱玲的人生三部曲,但《雷峰塔》与《易经》仍是一个整体,从书中人名与《小团圆》完全两样可知。” 逢甲大学中文系教授张瑞芬说。
宋以朗
选择直译而非“张腔”
《雷峰塔》和《易经》中文版的引言是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所写,他在引言中详细叙述了《雷峰塔》和《易经》手稿发现和出版缘由。宋以朗写道,“一九九五年九月张爱玲逝世,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在其遗物中找到《The Fall of the Pagoda》(《雷峰塔》)及《The Book of Change》(《易经》)的手稿后,便按遗嘱把它们都寄来宋家。”“读这叠手稿时,我很自然想问:她在生时何以不出?也许是自己不满意,但书信中她只怨‘卖不掉’,却从没说写得坏;也许她的写法原是为了迎合美国广大读者,却不幸失手收场;也许是美国出版商(如Knopf编辑)不理解‘中国’,只愿出一些符合他们自己偏见的作品,结果拒绝了张爱玲。无论如何,事实已没法确定,我唯一要考虑的,就是如何处理这些未刊稿。”“我选择出版这两部遗作,而读者也可按不同理由选择读或不读。这些理由是什么,我觉得已没必要列举,最重要的是我向读者提供了选择的机会。”宋以朗昨天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,“出版《雷峰塔》和《易经》主要目的并不是文学问题,而是解决一个历史问题,那就是当年在美国的张爱玲还是一直在写作,写了这两部书,但被美国出版机构拒绝了,我想向读者表明,那个时候的张爱玲写了什么。”
将《雷峰塔》和《易经》翻译成中文在华语地区再出版,之前有诸多评论对此举有非议,但宋以朗在引言中说,“无可否认,张爱玲最忠实的读者主要还是中国人,可惜有很多未必能流畅地阅读她的英文小说。没有官方译本,山寨版势必出笼。要让读者明白《雷峰塔》和《易经》是什么样的作品,就只有把它们翻成汉语。”对于翻译是否需要“张腔”,宋以朗倒是坦率表示,他的选择是直译,“我们的翻译可以有两种取向。一是唯美,即用‘张腔’翻译,但要模仿得维肖维妙可谓痴人说梦,结果很大可能是东施效颦,不忠也不美。二是直译,对英语原文亦步亦趋,这可能令中译偶然有点别扭,但起码能忠实反映张爱玲本来是怎样写。不管是否讨好,我们现在选择的正是第二条路,希望读者能理解也谅解这个翻译原则。”而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,宋以朗对如何翻译向早报记者解释,“张爱玲还用英文写了散文《重访边城》,后来我又找出来了她自己用中文再写一遍的《重访边城》,我觉得没人能把这篇文章翻译得像张爱玲自己写的一样,因为没有人可以写出张的中文。”
《雷峰塔》和《易经》译者并非是外界猜测的知名作家,而是台湾知名译者赵丕慧,她在台湾翻译的作品包括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、《幻影书》与《赎罪》等。对于赵丕慧的翻译,宋以朗对早报记者表示,“赵小姐翻译张爱玲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。”
张瑞芬:伤害她更深的,其实是母亲
逢甲大学中文系教授张瑞芬以《童女的路途》一文做了《雷峰塔》与《易经》中文版的导读,导读引用了《易经》中一段触目惊心的话:“琵琶尽量不这样想。有句俗话说:‘恩怨分明’,有恩报恩,有仇报仇。她会报复她父亲与后母,欠母亲的将来也都会还。许久之前她就立誓要报仇,而且说到做到,即使是为了证明她会还清欠母亲的债。她会将在父亲家的事画出来,漫画也好……”原来,化名“琵琶”的张爱玲打小就打算着把家事都写出来,以此来报复“父亲与后母”。张瑞芬在导读中也表示,看完《雷峰塔》与《易经》,“一股冷凉寒意,简直要钻到骨髓里”。“如果书中属实,舅舅和母亲无血缘关系,是抱来的(这点《小团圆》也说了),弟弟也不是她的亲弟弟(那个可疑的教唱歌的意大利人……),母亲和姑姑在钱上面颇有嫌隙,姑姑甚且和表侄(明表哥)乱伦,有不可告人的关系。在这一大家子的混沌关系中,张爱玲像是逃出了疯狂牢狱,精神却停滞在孩童状态。她幽闭茧居,精神官能症或偏执狂般聚精会神玩着骨牌游戏,一遍又一遍的推倒长城,然后重建。鬼打墙一般,非人的恐怖。” 张瑞芬剧透说。
对于小说本身质量,张瑞芬继续剧透,“熟知张爱玲的人,读《雷峰塔》与《易经》,初初会有些失望(大致不出《私语》、《童言无忌》和《对照记》内容)。读张爱玲这部形同《私语》和《对照记》放大版的自传小说,最好把自己还原为一个对作者全无了解的路人甲,愈不熟知她愈好(正如读《红楼梦》不要拿荣宁二府人物表焦虑地去对照曹雪芹家谱)。”
《雷峰塔》与《易经》里没有了胡兰成,最大的看点可能是张爱玲与母亲的关系,“一般人总以为父亲和胡兰成是张爱玲一生的痛点,看完《雷峰塔》与《易经》,你才发觉伤害她更深的,其实是母亲。” 张瑞芬说。《雷峰塔》起首是母亲出国离弃了她,《易经》的结尾则是战事中她拼了命回到上海那栋母亲曾住过的公寓。“在《易经》里,一个首次坦露的具体情节,是母亲杨露从国外回来探视正读香港大学生活拮据的琵琶,当时历史老师布雷斯代好心资助了琵琶一笔八百元的学费,琵琶将这好不容易得来的一点钱全数交给了母亲,后来竟无意间发现母亲轻易把这钱输在牌桌上了。杨露以为女儿必然是以身体作了交换,她催促琵琶亲自前往老师住处道谢,之后并偷偷窥看琵琶入浴的身体,想发现异状,这事却使琵琶感到羞辱极了。 ”